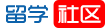为什么这里的人如此沉默?德国诗人布雷希德于1940年间在芬兰13个月的流放日子中就已经表达出这种迷惑。他的一句“一个用两种语言沉默的民族”从此成为芬兰的谚语。在整个欧洲,芬兰人的沉默由阿基的电影而闻名,在他的电影里,有时突如其来的静默可以长达20分钟,主角保持缄默,一直等到最后的几句结束语才打破沉寂。情侣们互相依偎着,整天除了在一起不停地猛灌咖啡外,少有互相交谈的沟通。在百无聊赖的旅途中,芬兰的火车或是电车简直就是充满死一般寂静的地方。即使当整个车厢都塞满人时也一样。旅客们一动也不动坐着,他们遥望窗外,视线绝对不和对面的人交汇,车厢中也没有人开口说话,当有人要下车时,只要半转身子,对邻座的人稍微望一下,旁边的人马上就能够理解并立即起身让开。在芬兰的火车上,从陌生人那投来的眼光简直是不可思议的,有的话,也是因为有某种意义或目的。
最佳电话用语
沉默的芬兰人将整个城市营造得像冷酷的地窖一样,只除了大街上。初到芬兰,对于芬兰街道的第一印象是“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牙痛?”再仔细一看,才发现他们的手并非因为牙痛而捂住脸颊,而是用来握着移动电话。他们看起来不像是我们国家那些忙碌的商务人员,反倒像是衣衫褴褛、戴着皮帽、表情忧伤的落寞者。每个人都热烈地交谈着,举止合宜,毫无禁忌。这是一个喜欢沉默却热爱打电话的民族,这种矛盾的情形是对芬兰人的最好描述。
裘伊斯是芬兰流行音乐界的老大哥,他是在70年代第一个用芬兰母语唱流行歌曲的人。裘伊斯喜欢他的母语,因为它是如此困难,在含义上也极端艰涩,清楚的轮廓下有着不变的意义。“我们芬兰人,”他解释到,“在交谈中很少有大的手势,为什么?因为我们的语言意思已经够明显了。我们也不说‘别客气’、‘您可不可以’或‘您真是一个好人,如果能怎样的话’,芬兰语是用来打电话的最佳语言。只要三句话就可道尽所有事情。但用英文或法文就得滔滔不绝了。”裘伊斯对欧洲人轻易地说出“Love、Darling”不解,带点神秘而又不可思议的芬兰人和他们的语言是如此一致,当他们说出“爱”时,那确实是意味着他们从头到脚、一生一世的热情。夜晚当他们说要喝酒,他们就直接扯下瓶盖,喝光瓶中的烈酒,而其他不去喝酒的人就保持着一贯的沉默。
芬兰的SiSu精神
人们把这种精神叫作“SiSu”,这种芬兰人的原始个性一旦发挥,便会让事情一路朝好的或痛苦的结局而去。他们靠着“SiSu”猎熊、在封冻的海峡里驾驶破冰船、攻占世界的移动电话市场,或是打仗。同时,“SiSu”也意味着对固有事物的冥顽不化。直至今日,由于有严格的移民法规,芬兰仍是欧洲国家中外国人口比例最低的,大约与阿尔巴尼亚相当。
在70年代时,即使在天气好的时候,咖啡店的老板也不可以把桌子摆出来,而酒精类的饮料只能在国营的店里贩卖,所有供应酒类的店家必须在窗户上挂起窗帘,以免让路人看到里面的酒客;未经侍者的同意,客人不得换座位;也不准有跳蚤市场;除了在某些固定的日子外,不可以拍打地毯,当然更不可以谈论政治。芬兰总统不是用统治的方式,而是以一种原始神话中的神奇父权权威端坐于芬兰的王位之上。他是西欧民主政治里的特例,可以任由自己主导,甚至是在局势对他不利时暂停选举,而整个国家却不会发出一点抗议的声音。
今天的芬兰已经跃入高科技时代,电视机、无线电话以及晶片电子工业取代了木材原料、造纸和破冰船,成为芬兰外销的主力。整个国家以快速的电脑化和喜好创造发明而赢得了“欧洲的日本”的美誉。只有沉默依然存在。他们走过堆满脏雪的街道,将脸和手都包裹在毛帽和夹克里急匆匆地走回家。